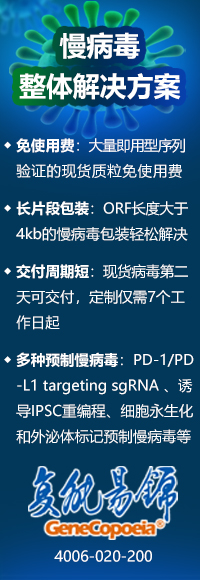伦理学研究——一条崎岖又漫长的发展道路
伦理学研究的发展,从最开始建立到如今进入个体化时代,已经成为了涉及每一个人的问题,Sarah Franklin撰写的这篇有关伦理学问题的文章,也因而成为了《自然》(Nature)杂志150周年纪念稿中的第六篇入选稿件。
在1869年的秋天,Charles Darwin正在辛勤地修订他的第五版《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同时也在撰写另外一本新书,即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当时,Darwin将他的这两份样稿送给她的女儿Henrietta进行编辑,希望Henrietta能够帮他防止可能会出现的敌对反应,比如Darwin认为,大自然是没有意识的,所以在大自然中也不存在道德与伦理的因素,这个观点可能会招致反对意见。
Darwin的表弟Francis Galton在1869年出版了《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一书。他在书中指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也可以用来研究自然规划(social planning)问题。Galton认为,人类的能力(abilities)在遗传上是有差异的,他为此还引入了统计学的方法来指导优生工作。后来,他又提出了“优生学”(eugenics)的概念,并倡导选择性生育(selective reproduction)。
Darwin那革命性的理论鼓舞了现代生物学;Galton将自然选择与社会改革(social reform)提到了同等的高度,并提出了优生学。但是这两个诞生于19世纪末的理论却引发了伦理问题,而且150年后,这个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甚至愈演愈烈。伦理与生物学之间从来就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就和150年前一样。区别在于,例如对未来子孙的改造,或者个人数据的监管等很多问题,都变得日益复杂。为了将来更好的发展,我们有必要先回头看一看。
19世纪末的社会也和今天一样,动荡不安,但是科学却在不断出现突破。之前有Darwin“骇人听闻”的理论出现,继而又陆续出现了一大批维多利亚时代的育种家、微生物学家、收藏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解剖学家,他们全都致力于通过各种精妙的试验,来发现生命的奥秘。英国剑桥大学的实验室演示者(laboratory demonstrator),兼博物学家Walter Heap为了检验妊娠对于动物遗传的形成性效果(formative effect),于1890年代,首次开展了胚胎转移试验。Heap将一种兔子的胚胎转移到了另外一种兔子体内。这也标志着破坏学习生物学(disrupt-and-learn biology)时代的来临。
生物学大发展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的历史学家Evelyn Fox Keller认为,20世纪早期就是“生物学的时代(the biological gaze)”。当时的试验不再是简单观察生命,而是开始对生命的各个部分进行干预和操控,以测试整个生命系统的极限,将各种成分混合在一起,将生物学调查了个底朝天。
1903年,胚胎学家Hans Spemann进行了著名的两栖动物试验。他用他女儿的头发,在蝾螈卵上打了一个结,结果这个卵最后长成了一个只有一条尾巴,但是有两个头的怪物。同样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美国生理学家Jacques Loeb也在开展他的生物工程学(engineering biology)研究,他用各种化学品和试验条件进行了试验,来促进海胆(sea urchin)等模式生物的发育。
在上世纪90年代培育出多利羊的Ian Wilmut也一度认为,多利羊的诞生将我们引入了可控生物学的时代(the age of biological control)。可实际上,我们早在1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过这种错觉。随着越来越精细、越可靠的生物学试验不断地向人体试验靠拢,科研界、产业界,以及政府监管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给伦理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20世纪,从不缺乏反对者的优生学,越来越成为了世界新秩序里的重要一环。从美国印第安纳州1907年的优生法案开始,到后来纳粹德国的种族清洗运动,都隐藏着优生学的身影。
优生学还给我们带来了各种人口管理手段,例如人口统计(demography)、种族分类(racial classification)、统计建模(statistical modelling)等,再加上计划生育(family planning),所有这些概念都成为了现代与进步的代名词。从拉丁美洲到印度、中国和苏联,优生学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种族改良运动(improve the population)。优生学关于本地人和外来移民之间,在适应度(fitness)方面的理论假设,就是整个大英日不落帝国殖民统治的核心。户口调查员创造出了“种族(races)”和“部落(tribes)”这两个新概念,用来更加“科学地”管理人口。这些概念被非洲和东南亚的新兴国家采用,比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种族观念就深受其影响。
不过,正如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in Sydney, Australia)的历史学家Alison Bashford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Philippa Levine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的思维方式不再会采用优生学那种狭隘的人口分类方案。现在大家普遍都使用目前就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社会学家Troy Duster提出的 “遗传力三要素理论(prism of heritability)”。即将精神疾病、同性恋、犯罪、贫穷、种族(ethnicity)、人种(race)等因素全都纳入人类(rational)这个范畴下,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不过,在上个世纪里被奉行的优生学运动背后的原则,也早就融入了我们当代社会的DNA当中。纵观世界各国一切与医疗健康、生育、教育、边境及监狱管理、地区发展有关的政策,无不贯彻着优生学的理念,即给人以选择压力(selective pressures),例如为外来移民打造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hostile environment)等。
胚胎学家Ian Wilmut在2015年的一次展览上,与他培育的克隆羊多莉的标本在一起。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的兴起
生命伦理学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最初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未获得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就对外来移民、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等弱势人群进行对身体有害的科学研究。而主战场就在美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1972年时被爆出,美国公共卫生署(US Public Health Service)曾经在1932年至1972年间,在美国塔斯基吉大学(Tuskegee University)进行过一项“秘密的”研究,他们一共招募了400多名患有梅毒的美国黑人男性(主要都是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穷苦的分成佃农),宣称让他们来参加临床试验,可以免费治疗他们的疾病,但是实际上却没有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治疗。结果有一半的人死亡,而且他们的妻儿中,也有60人染上了梅毒。这一消息公布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
1974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美国国家科研法案》(National Research Act),并且设立了美国国家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学科保护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两年之后的1976年,该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和操作指南,用于规范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种的各种伦理问题。
1978年,该报告以《贝尔蒙报告》(The Belmont Report)的形式在美国联邦注册杂志(US Federal Register)上刊登出来。成为全美国科研工作者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也诠释了现代生命伦理学的三大支柱,即尊重个人(respect for persons)、对个人有益(beneficence)和公正(justice)。该报告还厘清了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问题,并且为日后建立科学伦理强制监管制度打下了基础。这三大原则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对弱势群体进行不恰当的处置。在《贝尔蒙报告》的影响下,科研伦理也成为了现代科学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中心法则。
生命伦理学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涉及到了从公共卫生,到临床医疗的诸多方面,也在医学和科学训练,甚至在科学资助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后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政府对艾滋病危机那种迟钝、不力的反应,又进一步凸显了生命伦理学的重要性。
生命伦理学在此时积蓄起所有的力量,为器官移植、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等有争议的生物医学活动提供了指南。神学家Warren T. Reich在1978年出版的第一份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里,重点关注了临床医学上的一个关键点,即背离了保护生命的承诺。Reich认为,在过去,医学的原则是“不伤害(do no harm)”。但是在心脏移植出现之后,就出现了一个伦理学的两难情况,因为做这种手术既有可能会极大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有可能会要他们的命。与以往那种冷冰冰的医学伦理学观点不同的是,人生命的绝对价值现在变成了相对的了。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机构里,我们也可以为更高质量的生活而死亡。伦理学争论再度出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专业化的生命伦理学研究达到了新的境界。由公共科研基金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HGP)这个科研界的庞然大物,企图在20世纪末,彻底阐明Darwin和Galton的理论。伦理学宣称,HGP最大的一笔科研资助就是用于开展该项目对伦理、法律和社会(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ELSI)会带来何种影响的分析。仅在美国,就有大约30亿美元的经费(占到HGP整体预算的5%)被用来打造全世界最大的生命伦理项目。一大批生命伦理学家都在努力工作,试图弄清改变遗传物质(DNA或RNA),是否会对我们的后代造成影响,人工设计出来的婴儿是否会有害等问题。
到了上世纪末,又有一些新技术登上了历史舞台,比如克隆、干细胞及胚胎研究等新型生殖技术开始走向了舞台的中央。随着与HGP有关的各种转化项目的热度逐渐减弱,相关的生命伦理讨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当ELSI项目终止之后,生命伦理研究也失去了资金的支持。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1978年,当年除了有《贝尔蒙报告》出版之外,还发生了一件在生命伦理方面意义重大的事件,那就是全世界第一位试管婴儿宝宝Louise Brown出生了。在近50年来,最具争议的生命科研问题都与生育和发育有关。可是当生命伦理学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到HGP上之后,生殖医学又开始蓬勃发展了,也随之出现了很多类似于ELSI的有影响的缩略词。有一阵子,全世界对于克隆狗和转基因玉米的民意明显不同,可是对于基因修饰胎儿(GM baby)却没有那么明显。也许今后会有吧。
回过头来看,很多在上世纪末让生命伦理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焦点的力量,最终都会消退,例如基因期货投机(speculative genomic future)。近二十年来,生命伦理学已经进入到了未知的水域。今天,我们面临各种各样的生命伦理难题,比如基因编辑胎儿(gene-edited baby)、神经科技(neurotechnology)、人工培养类器官(dish-grown organoid)和纳米机器人(nanobot)等,科研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关系再一次走向了公众关注的舞台。
图中的小姑娘是世界上第一位试管婴儿Louise Brown,摄于1981年。
走出困局
就好像在19世纪末,现代生物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无法预计后果一样,我们现在对生命伦理学也感受到了同样的迷惑。由于缺少足够的政策和监管,那种被吞没的感觉也变得越来越强烈。生命伦理,这盏指路明灯也在逐渐暗淡下去,那感觉就好像《狮子王》中的小辛巴被淹没在狂奔的牛羚群中。今天,很多伦理学问题都与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之下,各国的监管政策却又大相径庭脱不了关系。未知的未知数,每天都在增加。
合适监管的标准从未降到这么低过,而且变得零散,各国针对从人工智能到转基因作物,都出台了细分的政策,像《贝尔蒙报告》那种单一式的指南恐怕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很多基础科研都是由私人资金资助的,因此也都是保密的。机器学习与生物合成技术的融合,又给我们出了新的难题。成功的国际监管案例也非常少。现在,我们已经出现了经过CRISPR 技术改造的双胞胎、有了人工合成的神经元细胞、有了自动驾驶汽车、僵硬的、官僚式的伦理监管已经不再适合当今这个世界了。
当然,生命伦理学也和其它学科一样,在不断发展。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就是融合,去权威化,更加灵活。生命伦理也不再依赖那些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相反,它变成了一块展示板,少了些专业性,多了跨专业性(interdisciplinary),少了多用途(multipurpose),多了证明(bespoke)。在科学上,我们正在“转向对话(turn to dialogue)”,可是生命伦理却往往更面向公众,反过来也一样。政策制定者、投票公司和那些就专门的问题(例如线粒体捐献等)组织起来,提供伦理咨询意见的政府半官方机构,都在评估生命伦理问题。杂志编辑、基金会、基金评审委员会和政策制定者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伦理裁判。发生这种转变有多种原因,而且已经发生了很长一段时间。其中就有英国哲学家Mary Warnock这些实干型的伦理学家(practical ethicist)带来的影响。Warnock早在1984年就为英国政府出版了《人类受精及胚胎调查委员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Inquiry into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在那之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John Harris就提出了抗议,他认为有些关键性的问题被模糊了,而不是被解决了。Harris指出,Warnock的调查方法太过于依赖“原始的情感(primitive feeling)”,这就使得她的结论非常危险,有很多错漏。按照Harris的观点,Warnock的调查委员会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体胚胎的道德问题(moral status),她们做了太多情感上的让步。
就我们所知,关于公众对于人体胚胎研究的情绪,Warnock是有预估的。她对多种相互之间有交叉的争论进行了研究,给新型生育技术的引入提出了严格的限制,这也让英国政府制定了一套更加灵活的准许制度,而且实际情况就是,英国政府的这套制度要比其它任何国家里类似制度的存在时间都长得多。Warnock的委员会里通常都有非科研人士参加,他们会遵照流程得出一个结论,判断是否同意开展一项有争议的治疗或试验。而这一决定也需要符合英国议会批准的、严格的、全面的行业准则。Warnock指出,法律本身就应该既是担保人,也是公共道德的象征,应该是容许范围(permissive scope)和社会道德观念(the moral idea of society)的精准法律表达的结合。这也是伦理学思考的新方式。
当英国政府决定,在1990年通过《人工生殖和胚胎法案》(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ct),但这并不能起到类似于美国国家生物伦理咨询委员会(US 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的作用。发育生物学家Anne McLaren也是Warnock委员会的成员,她采用了最流行的,也是最实际的做法来应对公众对科学的信任。
今天,跨学科的专家,以及更多更有创造力的公共咨询,也给伦理学引入了许多新的方法。这一趋势又被Nuffield生命伦理委员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等机构进一步强化。除了生命伦理和哲学之外,Nuffield生命伦理委员会还为英国政府提供多学科的咨询服务。自1993年起,该委员会已经就多种有争议的生命伦理问题,提交了近30份专业报告,涉及从遗传筛查(genetic screening)到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等多个领域。但是这些提交的报告中,很少是由生命伦理学家担任主席的。在很多报告里,关于什么是伦理问题,都拓宽了讨论的范围,比如,由英国剑桥大学植物学家Ottoline Leyser担任主席的,英国科研文化的探索。同样的,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也提供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行为国际指南,涉及监管、沟通、研究整合、患者福利、社会正义和对研究参与者的尊重等。
在当今这个社交媒体充斥的时代,我们时刻需要提防虚假新闻,新的杀手锏就是为有争议的研究(例如嵌合体胚胎、人脸识别技术等)创造信任系统的能力。在追求更符合伦理要求的同时,也需要构建更加透明的流程,对参与者更包容,对未知的事物持更开放的心态,以获取公众的信任。而不仅仅只是区分对不对,是不是应该。
简而言之,专业的知识和可靠的数据都是必须的,但是这还不足以建立一套持久的、人性化的管理制度(humane governance)。因此,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持续的沟通和向外延展,关注更加长期的策略,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阶段都给予反馈。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对专业伦理学家的依赖,可以更加关注不同的群体。
在实际运用中,比如心脏移植、肝细胞移植、对蚊子进行改造来抗疟、治疗亨廷顿氏病等,我们在进行权衡和取舍时,也对Darwin和Galton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发现,我们所共有的并不仅仅是生物学上的发展,或者对其进行改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承担着关乎人类乃至所有生物体未来的责任。这种新模型的意义是,大多数伦理学家其实都是最合群的,因此,包容性越高,科学性才越强,我们在一起才会变得更好,今天我们都是伦理学家。
原文检索:
Sarah Franklin. (2019) Ethical research — the long and bumpy road from shirked to shared. Nature, 574: 627-630.
Eason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