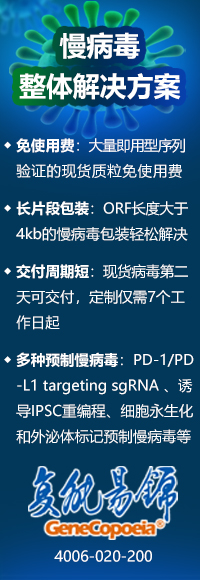实验室生涯:学成回国组建实验室
四位从海外回到东亚的研究人员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许多来自东亚的年轻科学家会在海外读研究生或者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回国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些东亚国家的经济蓬勃发展,为初入职场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四位最近回到东亚的研究人员接受了《自然》(Nature)杂志的采访,分享了他们在启动实验室时遇到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寻找有才能的实验室成员,并建立和保持合作关系等方面的经验。
Yue Wan:增加适应性
Yue Wan:新加坡基因组研究所(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结构基因组学家
在2013年我回到新加坡开办自己的实验室时,对于国内的文化氛围我感到非常欣慰,可能因为全球化,国内开放了很多。在此之前,我拿到了新加坡政府科学、技术和研究机构(A*STAR)的留学奖学金,去美国深造了十年,然后回国支持生物医学产业建设。新加坡在几乎没有自然资源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个以卓越、毅力和韧性为荣的世界城邦。
我在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圣地亚哥分校获得细胞生物学学士学位后,前往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于对酵母中的RNA结构进行全基因组测量(M. Kertesz et al. Nature 467, 103–107; 2010)。随后,我们开展了酵母中RNA折叠稳定性的研究,以及整个人类转录组(单细胞中所有基因的转录产物)中RNA结构的变异研究(Y. Wan et al. Nature 505, 706–709; 2014)。
大多数A*STAR获得者都会以博士后的身份回国,但在2013年,新加坡推出了奖学金计划,为新回归的博士学位持有人提供足够的资金,以立即开办自己的实验室。同年,我成为新加坡基因组学研究所(Genomics Institute of Singapore)的首位研究员。突然之间,我必须弄清楚如何雇佣人员,做预算,并维持实验室的正常运行。也就是一下子,我需要学习很多新知识。
独立研究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职位。我的大多数同事,包括我,都不知道独立研究员意味着什么。小组里没有博后,也没有首席研究员(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前任导师建议我通过在每次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言来刷存在感。这其实难度很大,对研究院里为数不多的女PI来说尤为如此。但我意识到,我有充足的资金来源,而且我也能独立做实验,于是我下定决心努力做下去。
新加坡的研究往往比美国的科学更注重实用性和转化性——聚焦在对社会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其中一个挑战就是为促进经济增长,每5~10年基金的支持倾向就会改变一次,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具有适应性。
2016年,我接受了A*STAR考察,然后获得了A*STAR为期6年、总金额达到600万新加坡元(折合44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升职成为高级科学家。我还获得了多项国际奖学金,其中包括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TH)的Branco Weiss奖学金,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科学妇女奖学金和EMBO青年研究者奖(EMBO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这些奖项让我能够与来自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开展合作。
我的实验室成立5年了,在这期间我生了两个孩子。新加坡目前为大多数公民提供4个月的带薪产假,但我放弃了产假。我担心如果我离开4个月,实验室进度就会停下来。每次生完孩子,我就休息3周。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每天工作两个小时,以帮助我的员工保持正常状态。两个月后,我就开始全职工作。
亚洲的家庭成员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的父母住在附近,很乐意帮我带孩子,并且这里请保姆的费用比较便宜。如果没有这些支持——我和我的丈夫(他新加坡基因组研究所(Genome Institute of Singapore)和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都有实验室)——就不可能投入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实验室上了。
NETHIA KUMARAN:最大化知名度
NETHIA KUMARAN: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Malaysia)癌症生物学家
在澳大利亚工作四年后,我回到了马来西亚。回国后,我注意到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和工程的重要性,并鼓励更多的女生学习科学。我本科学的是微生物学,从中了解到病毒可能致癌后,我开始对癌症生物学感兴趣。我在马来西亚科学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 Malaysia)读的本科,并打算找一位癌症生物学家做导师,但由于当时马来西亚这方面的专家比较少,所以未能如愿。
2005年,我本科毕业后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攻读肿瘤学硕士。马来西亚政府为在马来西亚境内或境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提供了全额奖学金。由于马来西亚的癌症生物学专家非常少,所以随后我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读博。我于2012年毕业,研究方向是癌症的细胞死亡途径。
我在澳大利亚有两位出色的导师。他们帮助我更好地阐述我的发现,让我学会合作,并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发言。我专注于构建我的人脉网络和协作。
我本来在打算先做一段时间博后工作,以获得更多的训练和经验,但马来西亚要求受国家资助留学的学者在完成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于是,2013年,我选择回到马来西亚理科大学(University of Science)做PI,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大跳跃。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坐落在美丽的槟城岛上——国内文化最自由的地区之一。
我在悉尼的导师告诉我,申请基金时最重要的不是研究细节,而是清楚地告诉资助者为什么你的研究很重要,它有哪些发展前景,以及为什么他们要给你提供资助。虽然这些建议对我帮助很大,但我仍然需要马来西亚的导师帮助我了解我们的拨款系统。在国内,文化和学术惯例和澳大利亚非常不同。这是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但我最终拿到了马来西亚理科大学和高等教育部(Ministry of Higher Education)的资金支持。
在我的五年PI生涯中,马来西亚的研究经费减少了很多,申请资金的竞争日益激烈,但我的实验室有两名博士生和两名硕士生。尽管我在国内确实有一些合作者,但马来西亚的癌症生物学仍然比较小众。我也有申请国际资金支持,但这需要国际合作者。全球合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时我给海外研究人员发邮件,但没有收到回复。
现在,我正在逐渐建立我的知名度。由于缺乏资金,我无法每年参加国际会议,所以2017年,我在马来西亚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在连续4年申请后,我终于在2016年获得了欧莱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女科学家奖学金(L’Oreal–UNESCO fellowship),这有助于提高我的知名度。
话虽如此,我还是要考虑离开马来西亚,去别的国家找教职。不过,尽管这里的岗位是终身性的,但是在国外更多的岗位却是临时性的。这点让我犹豫不决。理想情况下,我将在海外学习一段时间,掌握新技能,然后重新回国开拓我的事业。
MYUNGEUN SEO:保持竞争力
MYUNGEUN SEO: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所(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高分子化学家
2012年,我与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化学家,我的博士后导师Marc Hillmyer作为共同作者,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花了两年才完成,但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去深入研究一个问题。考虑到科学工作者发表论文的压力,高影响因子杂志上的论文只署两名作者的名字是很罕见的。(一般一篇高分论文都会有多个共同作者。)但我相信,是这篇论文帮我获得了韩国高等科学技术学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的教职,我在KAIST度过了整个硕士和博士生涯。
自2013年拿到教职以来,我很高兴回到拥有30多个国家实验室和工业研究中心的科学之都大田。作为KAIST的化学专业学生,我在访问日本和美国的实验室的同时,研究了如何将小分子自组装成纳米结构。2007年,在我的博士学位期间,我去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做了6个月的访问学者,在那里我学习了一种新型聚合方法——到现在我还在使用这种方法,它对我的研究之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发表的一篇论文(M. Seo et al. Macromolecules 41, 6413–6418; 2008),迄今引用次数超过100次。这些经历鼓励我申请国外的博士后,那篇《科学》(Science)论文就是2009年时在Marc实验室做博后时发表的。
四年后,我回到了韩国,KAIST的现场面试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日子之一。KAIST在和其他大学竞争那些在其领域内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科学家。现在韩国正在经历一波大退休浪潮,所以有很好的工作机会。
我用实验室启动资金购买了实验台、通风橱和一些关键仪器。我的实验室没有博士后或技术员,因为在这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我有13名来自印度的学生,其中4位是女性,1位是博士后。KAIST成功地将外籍学生、外籍教师和女教师的人数增加到了学校人口的10%,并且正在计划再增加10%。我努力让学生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去完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故事,就像Marc为我做的那样。自开始筹建我的实验室以来,在我发表的三篇论文中,学生都是唯一的共同作者(另一个作者是我)。
基金拨款情况每年都有变动——并且竞争非常激烈,成功率大约为10%。尽管如此,我不仅有个人基金,可用于继续开展基础研究,我参与的一个团队还获得了为期7年的1000万美元基金,用于探索自组装分子的化学结构。
我可能会在2020年申请终生教职。自从2008年KAIST纳米科学和技术研究生院成立以来,只有一个人成功拿到了终身教授职位。多发论文总是有用的,但质量比数量更重要,杂志的种类也很重要。此外,国际知名度也是获得终身教职的关键。今年3月,在美国同事的协助下,我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举行的美国化学学会年会(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组织了研讨会,聚集了来自各国的领域先驱,共同研究复杂聚合物如何自组装。
KIM HEI-MAN CHOW:保持联系
 KIM HEI-MAN CHOW: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神经科学家。2013年,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神经科学家Karl Herrup因其在Wnt信号传导(Wnt信号通路是调节细胞命运的关键途径)的工作而名声大振。
KIM HEI-MAN CHOW: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神经科学家。2013年,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神经科学家Karl Herrup因其在Wnt信号传导(Wnt信号通路是调节细胞命运的关键途径)的工作而名声大振。
尽管我是一位没有神经科学背景的癌症生物学家,但他还是雇用了我,希望我能为他的研究提供新的角度。
我在香港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时,学习过Wnt通路。在博士第三年,我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癌症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ancer Research)会议上介绍了我的研究,确定了一种可能调节Wnt信号的潜在药物靶点。
做完报告后,我收到了两个美国实验室的博士后邀请。
我选择前往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生物医学工程师Xiling Shen的实验室,但我对计算生物学或系统生物学方法完全不了解。我在康奈尔大学的经历革新了我的生物医学研究方法。
临床试验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一次只关注一件事。而系统生物学不一样,我们首先看的是整体,筛选基因或蛋白质是否是疾病的主要原因。然后我们使用分子生物学工具来集中研究。不过,在去康奈尔大学工作6个月后,我不得不回国照顾生病的母亲。我无法专注于全职研究,所以在母亲康复期间,我做了一年的医学编辑工作。
我在Karl实验室的第一年很令人沮丧,因为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大脑,但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学习新技能,并开展第二次职业生涯——应用系统生物学方法研究阿尔茨海默氏症。
根据我的经验,美国的学生和博士后倾向于更自由地探索与PI研究无关的想法。在香港,大多数学生从事的是他们的导师已经制定的研究。两种方式都有利有弊。香港吸引了很多外国专业人士,因为香港到东京、台北、首尔和新加坡等地非常便利。香港也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古老的传统与西方文化和后现代潮流相融合——对于像我这样的美食家来说香港是完美的。
基金申请也许是美国和香港差别最大的地方。在美国,会有一些联邦和非盈利基金资助小型项目,也会有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但在香港,基金来源比较少,并且大多数早期的科学家对国际基金知之甚少。
我在加入Karl实验室的12个月内发表了第一篇神经科学论文,然后拿到了美国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US Alzheimer’s Association)以及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基金支持。
过去三年来,我一直担任研究助理教授。这是一个介于博士后和完全独立的助理教授之间的“灰色”地带。我可以申请补助金,并独立开展我的项目,但我仍然隶属于Karl实验室。
我有申请其它基金,包括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基金来寻求合作,毕竟我想要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希望明年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维护国际人脉,我会在晚上和周末与潜在的国际合作者互通Skype电话。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我可以随时和Shen这样的同行联系。当你可以和同行亲自交谈,并一起讨论当前的研究时,这种联系更加强大。
我的目标是在开始寻找我的下一份工作之前,先发表一些高影响力的文章。香港是一个小地方,空间有限,同时来自中国大陆的研究人员大量涌入,竞争激烈,所以我对去其它地方寻找教职工作持开放态度。
原文检索:
Virginia Gewin. (2018)How to build a lab in East Asia’s science hot spots. Nature, 558:625-627.
张洁/编译